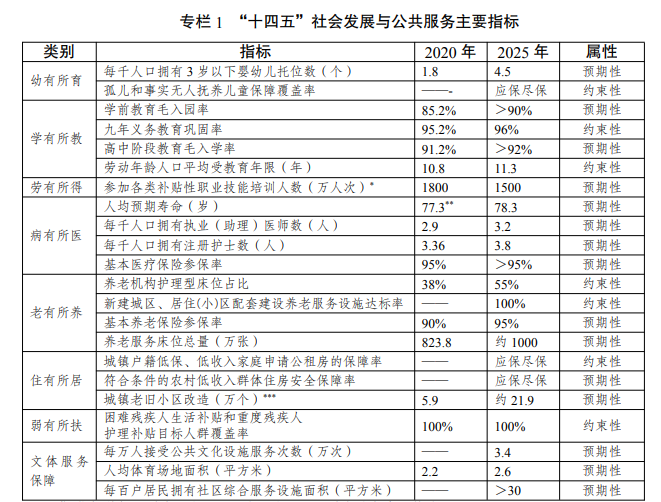这些年,弗洛伊德帮了多少编剧
在今年的高分剧集《漫长的季节》中,龚彪经常提到弗洛伊德和他的代表作《梦的解析》,以此来彰显自己90年代大学生的身份。精神分析作为现代知识术语,出现在他和丽茹的对话中;《梦的解析》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道具,可以挂在胸前防身,或者出现在关键时刻的单身宿舍的床上。
《漫长的季节》
 (资料图)
(资料图)
在这部剧致敬的《马大帅》第三部中,也出现在了精神分析。身在厨房、心向星空的范德彪,将这位远道而来的“解梦大师”供上神位。他认为自己与这位奥地利学者志同道合,在现实层面,后者还能给自己指一条创业的明路——帮人解梦。
《马大帅3》
在以上两部剧集中,精神分析凭借自己现代知识属性和与中国传统玄学的相似,起到某种符号化的作用。但是纵观影史,精神分析在电影中起到的作用并不是仅此而已。法国当代最重要思想家和艺术史家于贝尔·达弥施,在他的经典著作《落差:经受摄影的考验》中,就专门写道,精神分析是如何在电影中得到“表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
下文摘自《落差——经受摄影的考验》中的《紧迫感:研究提案》。
对于电影来说,(除了“加速”外,)还存在着其他“过分”的形式。首先就是对精神分析的使用,有时是一种戏仿,有时不是。它运用精神分析的花招、精神分析的手法,有时还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而且无须担心是否必须有一种对病人进行治疗的上下文背景。
精神分析是如何在电影中得到“表现”的,它如何在电影中介入,如何被搬上银幕,呈现出来,或者展现其作用?它在那里起什么样的作用?它必须完成什么样的功能,这些功能又是什么性质的?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涉及精神分析在银幕上的形象问题,而是这样一种搬上银幕、呈示出来或者展现其作用的做法的内容与结果。电影以潇洒、随意的方式,有时又以漫画的方式,向精神分析借用了一些装置与设备,以及尤其适用于它自身目标的手段,以至于在两者之间出现了一种秘密的默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体现出来——这在理论上还没有被探讨——而且不仅仅体现在剧本的层面,还持续了整个拍摄过程,直至最后的剪辑。
电影可以运用精神分析来昭示一些人物的行为动机,甚至解释其中某些人的行为方式;但是,精神分析也可以超越心理机制,成为一个在整体上或部分上以治疗为结构的剧情的动力之一,甚至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涉及的不是那些电影使用的向精神分析学的参照与借鉴,而是电影(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可以为无意识以及在构成它自身的“场景”的过程中提供的位置,而这一无意识自身的场景也就是电影的场景(这里用的是德里达在谈到弗洛伊德与写作的关系时提到的“写作场景”中“场景”一词的概念)。
电影肯定有一定限制的时间持续,要求行动的时间——甚至行动的地点——在行动以治疗的形式出现时,也被限制在一定的时间限制中,而精神分析过程其实是没有明确期限的。精神分析具有它的节奏,它自身的节奏,是一种与电影操作并不相符的工作的节奏,而且与电影操作使用的花招也完全不同。为了演示精神分析对电影的加速过程看上去有些悖论性质的贡献,我在此仅举两个取自好莱坞电影的例子,这两个例子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尤其特别。
如果说罗伯特·西奥德马克的《蛇穴》或者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爱德华大夫》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许多电影不同,还不太像一些电子游戏,那么,时间的张力,也就是说拉康所说的“紧迫的功能”,还是在其中以属于不仅仅是心理的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需求、另外一种结构的形式体现出来。在这两部影片中,情节都要求治疗的时间被彻底缩短。
比如在《蛇穴》中,为了治疗和收益的双重目的,因为传统的心理分析机构不能接受精神分析的缓慢进程,而且与电震疗法相比,效果一直都不是立竿见影的 (该影片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精神病医院状况非常精彩的描绘):于是,就命令医生尽快结束对一个女病人的治疗,致力于将她从电震疗法的可怕过程中解脱出来,结果医生所拥有的期限变成了只有一个星期。
《蛇穴》
在《爱德华大夫》中,格里高利·派克和英格丽·褒曼饰演的夫妇则只有两到三天的时间去证明丈夫的无辜,因为他是一种幻觉症的受害者,使得他成了谋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前往褒曼的老师那里,让病人去接受一种加速了的治疗,从收效的角度来看,就起到了一种挑战的作用,成为一种悬念的动力。在这两部电影中,无意识通过一种对人们想逼迫它接受的节奏的、至少是临时的抵抗形式而体现出来,以便在最后起到解决一切的“天外之神”的作用。
将有意识的回忆的正常程序(不算剪辑的效果)加快,以满足一种外在于精神分析机制的客观要求的想法,与在精神分析学的历史中不断出现的异端思想与行为具有相似之处:甚至分析治疗的持续工作不可缩减的时间流程中作为无意识的事实的突然短路问题,也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叙述动力,尤其在《爱德华大夫》中,涉及的是一个人命关天的生死问题,精神分析为电影提供了一种手段,后来希区柯克在《艳贼》中又重新使用了这一手段,虽然没有达到同样强的张力。
弗朗索瓦·特吕弗曾对希区柯克说,他不喜欢《爱德华大夫》中的剧情。希区柯克回答说 ,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对男人进行追捕的故事,只是情景使然,成了“伪精神分析的”。这样一来,我们在此就很难再有所发挥。但是,其实,这一说法与希区柯克在1944年回到好莱坞时所说的意图并不相符(特吕弗故意没有向希区柯克提起此事):当时他说要拍摄有关“精神分析的第一部电影”,选择本· 赫希特作为剧本撰写的合作者,在他看来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此人对精神分析十分感兴趣。如果希区柯克没有在这个剧本中放入自己的思想,那会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个剧情由于必须寻找一个事实真相,而这个真相又外在于精神分析所要求达到的目标,所以从反面利用了一种治疗模式,运用了一种加速的机制。
《爱德华大夫》
如果说存在着一种对治疗的反向理解,那么,它是故意的,以下事实就可以从反面加以证明:一方面,编撰得非常完美的剧情都是留有回味的(如由萨尔瓦多·达利构思的梦中的雪的场景),而且没有静场的时间;另一方面,希区柯克本人却像一个非常好的精神分析家一样,从容不迫,让主人公在乡间漫步,缓急有致,最后假装将无意识逼到了无处躲藏的状态(比如男女主人公两人初次见面不久后去野外散步的那个场景,一切都是为了通过褒曼性感的、张开的嘴,说出“肝泥香肠”这个词)。
超越“家庭主义”(俄狄浦斯情结)之上,电影为精神分析学打开的场景,从叙述的角度来看,与性别差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蛇穴》中,医生都是男子,病人与护士都是女性,影片的结局是女病人回到了她的男人身边,医生认为证明已经完成了一种成功的心理迁移 (“你看,你已经不再爱我了!”):在整部影片中,一直都有用图钉钉在墙上的弗洛伊德的照片,就像是一把进入剧情的钥匙,同时又像是一名见证人。
在《爱德华大夫》中,精神分析家与他的临时病人之间的分析治疗关系是通过一名女性来完成的,她本人也是一个精神分析家,她说话时,只是为了能够让无意识也有话说,因为在无意识中,封存着幻觉中的真相。重要的是,在这两部电影中,涉及的都是一种三者的关系,而且不论角色如何不同,都是一名女性、两名男子,只是在前一部电影中,病人是女子,后一部中,男子是病人。这一点是可以再加发挥的。
那么,在传统电影中面对时间与空间、时间流程与地点时的男女性别差异,又以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呢?就好像时间与空间是男人们的事情,而地点与流程是女性的问题:男人掌握各种机构的空间或者星球之间旅行的空间,但也掌握精神分析的空间;女性则进入疗养院这样的地点或者办公室的结构中。像这样的角色分工造成的结果就是语言的运用、掌握与说话权利的不同。《2001太空漫游》中的机制意味着女性虽然可以在理事会中获得一席之地,但也不能在里面说上话,在宇宙飞船中也没有她们的位置。在这一背景下,连电脑“哈尔”的声音也只能是男性的:将它想象成是女性的会改变情况,甚至改变整部影片的结构。
我们应当比较一下在《爱德华大夫》中的男女主人公亲吻之后的连续镜头和《2001太空漫游》中宇航员们到达了木星之后的镜头。除去表象不说,这两个同是代表“进入”的图像,究竟哪一个不是带有比喻性质的?是那些处于一条轴心上的门接二连三地打开,还是那些镜头仿佛陷入其中的对空间的开拓,而且还使用了与影片中在此之前的节奏形成鲜明对比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加速?
《爱德华大夫》《2001太空漫游》
后者是对过渡到了时间与空间的另一边的隐喻,最后进入了一个从装饰上看不出是哪个年代的墓中,在一个现代风格的栅栏上,挂着一些洛可可风格的家具与画作的摹作,在这个坟墓中,生活仿佛一直在延续,超越于死亡之上(通过宇航员脱下宇航服、不再用呼吸的辅助装置表现出来),体现为各种植物,而且处于一种绝对的孤独之中,然而才出现了整部影片或整个故事的对象,正如热拉尔·瓦依克曼所说的“世纪的对象”:一个完全是极简抽象主义的物体,因为这一长方形的石碑(它是从哪里来的,是用什么金属制成的?)在旅行的尽头才出现,插在地面中,没有任何生殖器象征的其他特点,只有它的垂直性。
在《2001太空漫游》中,据说可以永远不出错误的电脑是它的“主人”们设计好程序,在任何细节上管理、控制宇宙飞船的运行与整个太空远游的行程的,结果却好像出现了错误。这一错误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精神分析学上所说的口误。
后来,在情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了十分精彩的一幕:宇航员一步步地将电脑“哈尔”的功能切断,而电脑一个劲地告诉他,不要再继续下去,告诉他它的恐惧,后来又向他描绘,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它答应唱出它的主人教给它的儿歌,而且声音越来越慢,最后完全止住了(这里我们还是可以明白,为什么此时不可能出现女性的声音)。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哈尔”一被肢解,声音一停(这里一直是一个连接的问题,是能不能流通或者说不再流通的电流问题),一条消息就出现在屏幕上,就像是在默片中一样,最终使得宇航员彻底被留在了网络之外,并向他表明,一切都是预先设计好了的,包括这一事故,这一故事的背叛,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精心策划的结果。
《2001太空漫游》
故事的背叛。但同时也是语言的背叛,因为这条最后的信息彻底切断了语言,所有的空间都向语言封闭了。弗洛伊德在提到无意识的时候,说它是“无时间性的”,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是在时间之外的:有时候,在被译成法语时,被说成无意识是没有历史的。但是,无意识还是会将各种时间流程混合在一起,让它们相互渗透、混淆在一起(各种时间流程,在这里,必须使用复数,因为只存在特殊的时间流程和地点)。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它是“无空间性的”,是从空间中解放、解脱、脱离出来的,就像它是从时间中脱离出来的?但是,为了能将各种参照(不论是空间的还是时间上的)混合、混淆在一起,无意识还是需要一定的空间范围的。由于地点对空间来说,就相当于流程对时间的关系,所以地点的概念还是早于空间的概念而获得,因为空间被简化为仅仅是“自我”可以投射出来、投射在弗洛伊德所说的“表面”上的东西:也就是电影(电影可绝不是“无时间性的”或者“无空间性的”) 所能够呈现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射的概念是具有决定性的,而银幕与屏幕的概念也具有决定性。
所以,我们在此不是要披露许多电影(无论是好莱坞或是其他) 对精神分析所做的漫画式的歪曲,而是要利用这种往往是有意的粗放式的夸张,这种我们称之为“考验 ”( 从这个词的完整意义上来看) 的东西,以及电影以手段的名义对它的运用,对无意识有更多的了解。在西方,电影是与无意识相结合的,如同在东方,在一定的时期内,电影要与革命相结合。
在那部直到今天依然是阐述弗洛伊德经验的最好的电影,约翰·休斯顿的《弗洛伊德》中,剧本采取了一种长话短说的手法(这也是加速的另外一种形式),它将整个叙述都集中在精神分析的诞生时期上,与有关歇斯底里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应当将它与最早让萨特撰写的剧本,以及帕普斯特原来想与弗洛伊德一起拍摄、后来弗洛伊德又让给了卡尔·亚伯拉罕的电影相比较)。其具有十字路口般决定意义的时刻,在于从症状的领域到语言范畴的过渡。
《弗洛伊德》
按照德勒兹与瓜塔利的说法,歇斯底里的女性恢复说话的能力成了精神分析学的开始,正如患精神分裂症的男性的游荡,成了精神分裂分析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以男女的性别区别为基础的关系,也是有三个项存在,其中两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的:沙科或布罗伊尔/女病人/弗洛伊德。重点放在了话语在治疗歇斯底里症时所产生的突然、急骤的效果,至少这种突然性在影片中是明显的:话语终止了身体的症状,使其最终消失,仿佛以一个完全限于表面的特写镜头的效果,预示了后来精神分析学在人类话语空间中的拆卸工作。